在中华5000年文明中,棉花出现并不早。相传,魏晋南北朝棉花始入中国。而棉花的“棉”,最早见于《宋书》。大多时候,古人以“绵”代“棉”。
而就是这个“棉”,却在华农大放异彩。进入本世纪以来,棉花研究成为华农科研新的增长点。
1999年,我校的棉花分子生物学研究几乎是零基础;短短4年之后,第一篇SCI收录的研究论文诞生;2006年,在Plant Molecular Biology上发表论文;2014年,Nature Communications刊载了他们的重要研究进展;2017年3月7日,Nature Genetics在线发表了棉花团队重要成果。
岁月流金,厚积薄发。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我校棉花团队已经在同领域研究中成了国际“群雁”领头。
然而,但凡成功,背后总有一本发黄的艰辛“台账”,棉花团队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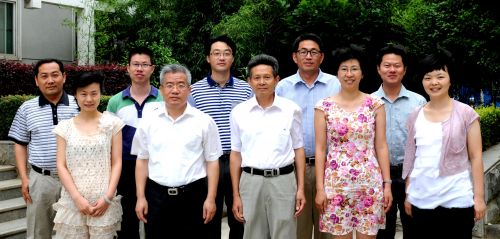
棉花团队合影
一个人一学科
华农的棉花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农学院时期,而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孙济中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棉花抗虫育种研究,并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重要奖项。
然而棉花研究在华农并非一帆风顺。1998年,随着孙济中先生的突然离世,棉花团队一时几近 解体,缺少了“领头羊”,棉花团队遭遇到了学科创立以来的严重打击。
棉花团队的事业,犹如一株棉苗,刚刚发芽出土欣欣向荣之时,却遭遇狂风骤雨。
正值困难时期,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他将“白手起家”,用他全部的青春与激情去支撑这个学科的发展。他,就是张献龙,时年35岁。撸起袖子干,他成了棉花团队的“掌门人”。
当时最难莫过于实验平台的搭建,1992年,他在刚刚成立的作物遗传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仅分得了1.5平方米的实验台,以此为基础,他带领着研究生开启了艰难的科学之旅。一个账本,全年科研经费不过20万,团队常常捉襟见肘,买一个国产的试剂盒都是奢侈品。
苦难不断,怎么办?缺少经费,他就四处争取,像挤牙膏一样对待经费用度。那时,他经常乘火车到位于河南安阳的中棉所出差。为节约时间,他常常坐晚上的“夜车”到北京和位于河南安阳的中棉所等地出差;为节约经费,他通常买站票或坐票,困了,就在车上打盹对付一下即可。第二天早上一到随即马上开展工作,并争取再坐“夜车”返回武汉。
1998年,聂以春教授加入棉花团队,科研“战斗力”得以“补给”。
彼时,棉花分子育种刚刚起步,张献龙和聂以春瞄准了这一国际前沿,开始布局棉花分子标记、抗病机制研究和以棉花远缘杂交高世代材料为基础的棉花杂交种培育工作。进入新世纪,团队又开始着手研究棉花纤维发育机制。
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许多在水稻、油菜等作物上简单易用的方法,如DNA与RNA抽取,在棉花上就是不适用。没有经验可遵循,亦无范式可套用,很多在棉花分子生物学上的研究技术都是棉花团队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从水中“淌”出来的。
团队虽小,但大家废寝忘我,坚守初心,辛勤浇灌的棉株终于结出殷实之果。
2003年,团队开始发表SCI论文,虽然影响因子不足1,但这标志着棉花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瞄准前沿,2006年,棉花团队启动非生物逆境抗性研究,2008年,团队启动生物信息和棉花抗虫生物学研究。
随着科研领域的深入,棉花团队也逐渐“扩容”:2003年,郭小平教授加入团队;2004年,朱龙付博士加入;2005年林忠旭博士加入;2006以后年金双侠、涂礼莉、杨细燕、闵玲、袁道军博士相继加入;团队人员增加到10人。
不但如此,团队研究方向不断完善,纤维发育、非生物逆境、抗病、抗虫、生物信息、基因组与进化、生殖发育、生物技术、分子育种、常规育种等,交叉研究得以全方位实现。
一位博士一个方向,一个教师一个亮点。一支将研究的上中下游联合、方向分工明确、梯度适宜的研究团队正在形成,一个发展中的学科生长点正在茁壮生长。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